合集:置身竞技场
纳瓦尔与 Nivi 围绕埃隆·马斯克、迭代学习与个人能动性展开的对话,讨论如何在实践中打磨直觉与优势。
合集:置身竞技场
原文:Collection: In the Arena(2025 年 10 月 14 日,nav.al 发布)
Nivi: 欢迎回到《纳瓦尔播客》。我翻出了纳瓦尔过去一年在推特上的一些发言,我们逐条聊聊他的最新思考。
灵感层层递进
Nivi: 先从这个问题开始。你说你拿到了埃里克·约根森提前寄来的《埃隆传》样书,读到什么出乎意料的内容了吗?
纳瓦尔: 我才看了大约 20%,但已经很棒了——书里几乎都是埃隆本人的原话。贯穿其中的是强烈的独立、自主和紧迫感。
这些内容不是教你照搬步骤的指南,因为他的做法为他、为 SpaceX、为特斯拉量身打造,离不开具体语境。但看到他毫不妥协、穷追猛打、对速度与迭代近乎偏执,就会被激励着站起来,让自己的公司也跑起来。
好的书都能唤起这种冲劲。听乔布斯演讲会让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;读埃隆的执行方式会让我想执行得更好,然后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路径。细节未必可复用,但真正有力量的是启发。
Nivi: 有趣的是,很多人觉得你既能给人灵感,又能提炼出大家真能用的原则。
纳瓦尔: 我的原则刻意保持在高层次,也不追求完整。一来更好记,二来也更通用。《如何致富》那套内容的问题在于,大家在 140 或 280 个字符里问我高度具体的问题,而我拿不到足够背景,没法给出负责任的回答。
这些东西都需要语境。所以我喜欢 Airchat、Clubhouse,也喜欢直播语音问答。在 Periscope 上,别人提问后我能反问一遍,再顺着挖,直到搞清楚真正的问题。然后我会说:“基于我掌握的信息,如果我是你,我会这样做。” 大多数情况都是高度情境化的,复制别人的细节没意义,原则才是可迁移的,所以我只讲原则。
事实上,作者埃里克做得很好,他把很多易引用的句子单独拎出来,等于把埃隆的推文再整理一遍。但最终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风格。埃隆有他的表达,我有我的方式。可能我能激励到某些人,我也会被他人激励——灵感是层层传递的。不过轮到执行,就得自己下场。
人生在竞技场里展开
纳瓦尔: 人生要在竞技场里度过,唯有实践才能真正学到东西。光靠读书吸收的知识过于抽象,最后只剩下贺卡式的漂亮话,你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用、在哪儿用。
很多所谓的“原则”和“建议”都不是数学那样的严密概念。我们说“富有”“财富”“幸福”“爱”的时候,语义经常重叠。既然谈不上精确定义,就不可能写出一部人人照做就能成功的剧本。你必须判断在什么情境下应用它们。正确的学习方式,是先做,再在过程中摸索“应该怎么做”。
做到一定程度后,你再回头读我的推文、读德意志或叔本华,才会突然明白:“哦,原来这句话讲的是这个道理。这条原则应该在类似场景里使用,它不是百分百准确的指令,而是一条能帮我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做判断的启发式。”
你先靠推理,再慢慢累积判断力。判断力足够成熟后,就会沉淀成直觉、品味或第六感,你最终依靠的是这些直觉。但前提是从具体行动开始,而不是停在抽象概念里。
如果你只读原则、格言、手册,不去实践,就会像我那条推特里说的那样——读书读得太多,反而迷失方向。你会把知识用错地方,成了塔勒布口中的“高学历傻瓜”(Intellectual Yet Idiot,IYI)。
Nivi: 我正想引用那条推特,6 月 3 日你写过:
“获取知识很容易,难的是知道在什么时候应用哪一条。
所以真正的学习都发生在工作中。
人生得在竞技场里度过。”
纳瓦尔: 那条推其实我本想只写“人生得在竞技场里度过”就发出去。但因为罗斯福那段“竞技场中的人”很有名,我还是想从自己的角度多解释一句。这是我不断重申的体会。
想学就去做
纳瓦尔: 我最近又创办了一家公司,项目很难,我们叫它“不可思议公司”(Impossible, Inc.)。这段经历又把我推入学习的狂热状态。我更频繁地追问 Grok 和 ChatGPT,读更多书,听更多技术播客,不停地脑暴,整个人精神高度活跃。甚至愿意在投资之外多见些公司,只因为能从他们身上学习。
这种“在做事”的状态自然而然地激发我去学更多,而且并不会让我觉得痛苦或透支。做事带来学习的欲望,也带来行动中的学习。而如果你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,很快就会失去动力——味同嚼蜡。
我们是“生物机械体”,我走路时脑子反而更快。按理说运动会消耗能量,效率应该降低,但事实不是这样。最好的头脑风暴,常发生在一边走一边聊的时候,而不是坐着不动。所以“做”和“学”相辅相成。如果你想学,就先去做。
多数难题要迂回解决
纳瓦尔: 生活中大多数有趣又困难的事情,解法往往不是正面硬撞。
这也是《如何致富》推文串里想表达的:如果你想赚钱,别直接盯着钱。你当然可以像金融掮客那样,但如果你是创造价值、利用杠杆、承担责任、发挥专长,财富就会作为副产品出现。你会做出好产品,把自己产品化,钱自然随之而来。
想快乐也是一样——不是盯着“我要快乐”,而是选择高流动性的活动,让自己投入其中,快乐就会冒出来。追求关系也是如此,你不会上来就说“我想和你睡觉”;争取地位更不能刻意炫耀,因为显得低位。
当然,并不是所有目标都得间接达成。有些事就是直接去做:想开车就上车,想写作就坐下写。但那些竞争激烈、又显得遥不可及的目标,往往正因为必须绕个弯。
真正在为自己工作时
Nivi: 4 月 2 日你写过一句推:“当你真正为自己工作时,你不会再有兴趣爱好、周末和假期,但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工作。”
纳瓦尔: 这是每个创业者或自雇者都体会过的悖论。你放弃了“工作 vs. 生活”的二元分法,再也没有朝九晚五,没有办公室,没有人告诉你下一步做什么,也没有现成的手册。同样地,你也无法按下暂停键。你就是企业、产品与工作本身,当然在乎它。
如果做的是发自内心的事,你就会投入得停不下来,这也是创业者的“诅咒”。好处在于,只要你做对了——目标、伙伴、方式都对——又能暂时放下没达成指标的压力,那它就不像“工作”,而更像是全情投入的创作。生产力最高的时候,是你只用成果来衡量自己,并且只对自己设定的标准负责。因此它既刺激又自由。
这就是我曾说过的:“尝过自由的滋味,就再也回不去打工。” 一旦你体验过不需要老板、不需要流程、不需要安全网的状态,你就再也无法忍受传统意义上的工作,哪怕是在小团队里高度自驱的创业者也是如此。
Nivi: 我觉得这句话还有层隐藏含义。大多数人看到“真正为自己工作”,会理解成“你是自己的老板”。但我读到的是:你的劳动是自我的延伸,是自我表达,而这很难摸索。
在行动中找到独特知识
纳瓦尔: 我一直相信,每个人都该找出自己独一无二、与本性契合、能够带来真实优势的能力,并勇敢地押注在上面。但你通常得先做了,才会发现它是什么。
这就是“人生在竞技场里度过”的真正含义。你只有在各种困难情境中行动,才会发现:“原来我能处理别人觉得棘手的事。” 或者别人会提醒你:“你的超能力似乎是 X。”
我有个朋友创业很多次。说他不聪明不专业也不对,说他不够努力也不对——其实他非常拼。但我注意到,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勇气。不管遇到什么阻碍,他都不受影响,总是笑着往前冲。百年前的人会说:“他最适合冲锋。” 放到创业场景,就是他能把头一次次撞在销售墙上,打 400 个电话被拒 399 次也不气馁,只要有一个“好”就够,然后继续迭代。
这就是他的“特定知识”。这项能力能让他在特定场景里不可替代。如果他能进一步组合其他优势,或者把它用在最需要的地方,他的独特价值就更明确了。你也一样,只有不断行动、不断上场,才能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知识和做事方式。
你得爱得发狂
纳瓦尔: 以营销为例,它是开放问题。有人拍视频,有人写文章,有人举着广告牌站在街头,有人办派对靠口碑传播。对你的业务而言,也许某种方式最有效,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与你天性契合的方式。
很多朋友找我合办播客,我会先问:“你真的喜欢说话吗?是发自内心地热爱长时间交流吗?” 否则你撑不住,也做不好。他们只是想做市场推广,于是开了播客,录两三期就放弃。听众也听得出来主持人并不享受对话,只是在完成任务。
如果你想做到顶级,就得喜欢得近乎“变态”。乔·罗根是最好的例子——即使没观众,他也会录节目。早年他就在 Ustream 上直播熬夜聊天,完全出于热爱,所以他才能成为头号播客主持。
所以做营销要顺着你的特定知识与天性来:喜欢聊天就做播客;喜欢对话就试试 Twitter Spaces 这样的直播;喜欢写作就上 Substack(长篇)或 X(短篇);喜欢视频就用最新的 AI 工具做视频。选个你真的热爱的领域,或在团队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、合伙人。现代世界的选择无限多,你要靠不断尝试、不断在竞技场里解决问题,才会逐渐缩小范围,找到那个既擅长又喜欢的事。
暂停—复盘—再出发
纳瓦尔: 我们之前聊过“成为你所做领域的世界第一,不断重定义自己的领域,直到这句话成立。” Akira the Don 还把它做成了歌。这条原则想要成立,前提是你不断迭代。
迭代不是机械重复,不是“花一万小时”,而是“一万次循环”。你做完一次,就停下来复盘:哪些奏效、哪些失灵;然后调整,再试,再复盘。所有学习系统都遵循这个模式。
进化就是一种迭代:变异—复制—选择,淘汰不奏效的变体。技术创新也是如此:提出新技术、尝试规模化,要么活下来,要么被市场淘汰。德意志讲的“寻找好解释”也一样:提出假说,经受批评,再删掉行不通的部分——这是科学方法的本质。
对个人来说,就是在竞技场里保持高度能动性,不断迭代,直到你成为最懂“自己”的人,而“自己”就是最终的产品。
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,守住能动性
Nivi: 还有一条我特别喜欢的推文,我当时还转发了。人们之所以想转推,往往是因为它说出了自己心里模模糊糊的想法。这条是 1 月 17 日的:“把一切归咎于自己,才能守住你的能动性。”
我的理解是:当你对所有事情负责,你才有资格、也有空间去解决它。如果你宣称“这不是我的问题”,那就轮不到你出手。
纳瓦尔: 你说的这种“终于有人把我的潜意识说清楚了”的感觉,爱默生经常做到。他有句名言:“每一部天才的作品里,我们都能认出自己曾经弃之不顾的想法,它们以陌生而庄严的面貌回到我们面前。” 我也想在推特上做这件事:说真话,而且用有趣的方式表达,最好还能带点情绪,这样既对得起自己,也有机会帮到别人。
很多人愤世嫉俗:富人都是骗来的;身世不利就注定爬不上去;出身某个国籍、族裔、身体条件的人没有机会……现实确实不公平,世界也不是靠纯运气运转。但我们都经历过:自己做的一件事带来了好结果,如果没做就不会发生。所以你完全可以改变局面。投入得越久、迭代越多、思考与选择越深入,运气的影响就越小。
拿硅谷举例:二十年前我遇到的所有年轻天才,如今无一例外都成功了。我真应该把他们按聪明程度建个索引,这其实就是 Y Combinator 在做的事。坚持二十年,能动性是有效的。你可能会说:“那是硅谷的幸运。” 可没有人天生在硅谷,他们都自己搬来的,只因为想靠近其他高能动的人。问题是很多人撑不住那么久,所以需要更高的动机支撑——这就是为什么埃隆要去火星、萨姆要造通用 AI、乔布斯在八十年代就想做一本大小的电脑。
犬儒心态会自我实现。就像骑摩托时盯着墙看,你最终会撞上去。所以必须守住能动性——守住那种“我能改变事情”的信念。孩子天生就有能动性,看见想要的东西就去拿。要把这种能力保留下来。
欺骗不了大自然
纳瓦尔: 你得对所有坏事负责——这是一种心态。它也许有点“自我催眠”,但非常有用。甚至进一步,把所有好事都归功于运气也没坏处。但别过度自欺,真相仍然重要。
事实是:长期努力、不放弃、对结果负责的人,最终都会在自己专注的领域取得成就。所有成功者都知道这一点。费曼常说自己不是天才,只是一个很用功的男孩。当然,他确实非常聪明——聪明是必要条件,但不是充分条件。我们太熟悉“聪明却懒”的人了。把潜力转化成动能,反而会提升你的潜力,因为人不是静止的,你会在实践中学到更多。所以别再找借口,上场就对了。
Nivi: 你也很喜欢叔本华。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?有什么让你意外的吗?
纳瓦尔: 叔本华不适合所有人,而且他写了很多类型的作品。有专门写给哲学家的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,也有像《论存在的虚无》这样的实用文章。我欣赏他的一点是,从不掩饰。他写下自己认为的真相,虽然不总对,但绝不撒谎,这种坦率能感受得到。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,只在乎“我写下的,是我确信的真理”。
很多人说他悲观,我不完全赞同。即便他的世界观看起来悲观,我读他,是为了摄入一剂强效的真话。他让我彻底接受“做自己”这件事。他毫不理会大众的看法,那种不屑的态度溢于言表。我未必那么精英主义,我更平等一些,但他确实给了我做自己的许可。你擅长什么,就别害羞,承认它。
这其实不容易。我们都想融入群体,就会避免出头——“出头的椽子先烂”。可如果你想做成非凡的事,就得在某种意义上押注自己。你当然不能自我欺骗。投资圈里常遇到自称“我特别厉害”的人,结果很脱离现实。是不是优秀,终究得别人说,而且亲妈不算。
来自别人的反馈往往不可靠。奖项、评论、亲友的夸奖都可能是真心,但被大量噪声稀释掉了。真正可靠的反馈只来自自由市场和大自然:物理很严苛,要么产品运作,要么失败;市场很诚实,要么有人买单,要么没有。其他地方的反馈都不算数。你若是为了上杂志封面或拿行业大奖而优化公司,那就走偏了。你需要的是客户,需要自然界的检验。火箭到底发射成功了没有?无人机飞起来了吗?3D 打印件是否达成成本和精度目标?骗得了一时,骗不了大自然。
好作者珍惜读者时间
Nivi: 跟叔本华不同,你算是“工业哲学家”,像工业设计师那样为大众服务。很多人让我们去读亚里士多德或维特根斯坦等经典哲学家,但我读完收获不大,反而在推特上跟你这样的思考者对话更有价值。想学哲学的朋友,我都会推荐先看大卫·德意志。
纳瓦尔: 你说得没错。我也看不下你提到的那些哲学家,包括柏拉图。其他哲学书我大多很快就放下了,因为他们常为了细枝末节争论,用晦涩语言搭建自洽体系。叔本华与其他哲学家对话时,也会掉进这个陷阱。我最喜欢他写短篇随笔的时候,那时候的他像极了玩推特:观点密度高、例子精炼,读一段能想一小时。我因此成了更好的作者、思考者和看人识人的观察者。
他毕竟写于十九世纪早期,涉及科学、医学、政治时难免过时。但谈人性时依然适用。我建议,想了解人性就读经得起时间考验的“林迪作品”;想获得专门知识、靠它获取报酬,就要紧跟前沿,因为这些知识更新快,也更容易失效。
我不太看那些既不古老、又不是人性主题的书,也会避开信息密度低的内容,比如多数历史书。我喜欢威尔·杜兰特的《历史的教训》,因为它是十二卷《文明的故事》的浓缩版。我读过足够多历史,知道他在说什么,所以不是盲目信。到了人生这个阶段,我希望读高密度的作品。也许看起来像是短视频时代的毛病,但更像是对时间的尊重。我们已经有大量数据和知识,现在要的是智慧——能和脑中信息互相连接的普适原则。
我喜欢的作者都极具信息密度。德意志、博尔赫斯、特德·蒋都是如此。老一代的尼尔·斯蒂芬森也是(后来则是信息量与篇幅齐飞)。最好的作者会尊重读者的时间,叔本华就是这一类。
大多数书适合速览,少数值得反复咀嚼
Nivi: 若想了解当代最尖端的知识哲学(也叫认识论),其实跳过其他人,直接读大卫·德意志就够了。
纳瓦尔: 我同意。如果你只想搞懂认识论,读德意志就行了。当然,对某些人来说,了解历史脉络和反方观点会更有帮助。像“知识就是被证明的真信念”或“归纳法”这些理论已经深深写进我们的教育和日常经验里。太阳每天升起,我们就觉得明天也会升起,这太符合直觉了。
所以很多人读德意志时,会看到他拆这些理论,但自己未必打过基础,容易怀疑是不是有反例。当年我第一次读德意志,也没完全读懂,把他当成物理学家写的一般科普书,与保罗·戴维斯、卡洛·罗韦利放在一起阅读。后来才发现我错了——他构建的是一套严密自洽的世界观,各部分互相支撑。
所以我建议先读德意志;如果一时难以接受,再去读其他人,然后回头重读,你就会发现他是怎么回答那些问题的。他自己会把功劳让给波普尔,说“我只是在重复波普尔”。但在我看来并不完全一样。波普尔写作面向哲学家,我反而觉得他更难读。或许德意志和 Brett Hall 会不同意,他们觉得波普尔很清晰,但我个人读德意志更轻松,可能因为德意志在书里边写边思考,是在为自己梳理世界。
如果只读他的认识论,你也不会获得最大收益,尽管前三章确实是最好的入门。《走向无限》前几章和最后几章最容易读,中间讲量子计算、量子物理、进化那部分就比较难,需要你至少对科学概念不排斥。他在为多世界诠释辩护,大多数人对此并无强烈观点,也不了解观测坍缩,所以读起来会觉得艰涩。
我通读德意志的收获,是看到他的理论如何跨学科连成整体。他发展量子计算,是为了设计能证伪多世界理论的实验,需要想象一个量子 AGI 的大脑,于是推导出量子计算的框架。理论之间相互约束,这就是他所说的“好解释难以改动”。
好产品难以更改
纳瓦尔: “好解释难以改动”不仅适用于科学,也适用于产品。看看 iPhone,这个圆润的珠宝般的设计,自初代以来外形几乎没变,核心就是单一多点触控屏、内置电池、顺滑的手感,成为“口袋电脑”的柏拉图式理想。苹果和竞争者都尝试过各种变化,但真正的形态难以被改动。零件可以升级,可整体形式几乎不变,因为一开始就找对了答案。
有句经典的话,圣修伯里的观点:“飞机之翼的完美,不在于无可添加,而在于无可删减。” 那样的设计也是“难以更改”的。未来人类找到飞往火星的正确飞船设计时,我敢说,在突破性技术出现之前,它的高层结构与细节都将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轻易修改。内燃机如此,电动车如今也是如此。
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很多产品看起来越来越像,尤其汽车。并不是审美被社交媒体同化,而是大家都进风洞去找最小阻力的形态,于是变得相似,因为那就是效率最高、最难变动的答案。
优秀写作者也是如此——他们的作品结构紧凑、层层嵌套,像分形一样。你能吸收到的内容取决于你的水平。第一次读懂 20%,再读一次 25%,配合 Brett Hall 的播客 28%,再用 Grok 或 ChatGPT 深挖某段,变成 31%。知识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,你能吸收多少取决于双方的准备度。只要读得懂语言,你每次都能有所得。
找到最简单可行的方案
Nivi: 看看 SpaceX 猎鹰系列的猛禽发动机,不同迭代的照片一摆,就能发现设计如何从“容易修改”走向“难以修改”。最新版本几乎没有多余零件可调整,早期版本则布满可以改厚度、宽度、材料的部件。
纳瓦尔: 复杂性理论有个观点:自然界里运转良好的复杂系统,往往源自被简单规则迭代了无数次的系统。最近的 AI 研究就是例子——我们拿简单算法喂入海量数据,它们会越来越聪明。反过来,如果一开始就设计得很复杂,再想让大系统跑起来,就会崩掉。产品设计的工作,大部分是在不断迭代,直到找出那个简单可行的核心。过程中你可能加了很多没必要的东西,最后还得回头把噪音剥离。
个人计算设备也是这样。macOS 依然比 iOS 复杂得多,而 iOS 更接近理想的操作系统。当然也许未来基于大模型的操作系统,用自然语言交互,会更进一步。要想规模化,最终都要删减。猛禽发动机就是例子。
这也是埃隆的工作法:在优化系统之前,先质疑所有需求——而且必须追溯到提出需求的“具体的人”,而不是哪个部门。问清楚“为什么要这个要求”,能删就删。删完需求,再减少零件,之后才谈效率、制造、成本。
把产品从 0 做到 1 的关键,是有个人——通常是创始人——能在脑子里装下整个系统,理解每个组件的角色,知道移除 A 会怎样影响 B、C、D、E 的需求和约束。这种整体视角,在猛禽发动机、在特斯拉生产线优化故事里都能看到:他在生产线上铺睡袋,不是为了调机器人速度,而是追问“我们为什么要贴这块玻纤垫?” 一路追到噪音团队、热管理团队,最后发现需求早已过时,于是把零件彻底移除。这种事在复杂系统里太常见了。
很多人说自己是“通才”,其实是在逃避专精。但真正要做的,是成为“博学者”:在保持广度的同时,对每个专业至少掌握 80/20 的要点,才能做出明智的取舍。
Nivi: 我建议想获得这种“博学”能力的人,在学校里尽量学习适用范围最广的理论。
纳瓦尔: 我会更直接:去学物理。
学物理就是学习现实如何运作。有了物理底子,你可以快速拾起电机工程、计算机科学、材料、统计、数学。几乎所有领域里最优秀的人都有物理背景。即便没有,也别灰心——我自己算是“物理学习失败者”。但你还能走其他路径,只是物理能训练你直接面对现实,毫不留情地把虚假的念头敲掉。
社会科学里,你很容易抱着一堆稀奇古怪的观点,即便用了复杂数学,也可能 10% 真、90% 假。基础物理其实不用深到夸克或量子,经典力学就够了,是很好的底层课程。
当然,任何 STEM 学科都值得学。如果已经过了求学阶段,就和别人组队。最优秀的人往往也是动手的“修补匠”——他们总是在用最新工具、最新零件造酷东西。比如在无人机成为军用前就开始做竞速无人机的那批人,在机器人上场前就造格斗机器人的人,或者为了把电脑搬回家而自己组装 PC 的人。他们才是理解世界、推动知识前沿的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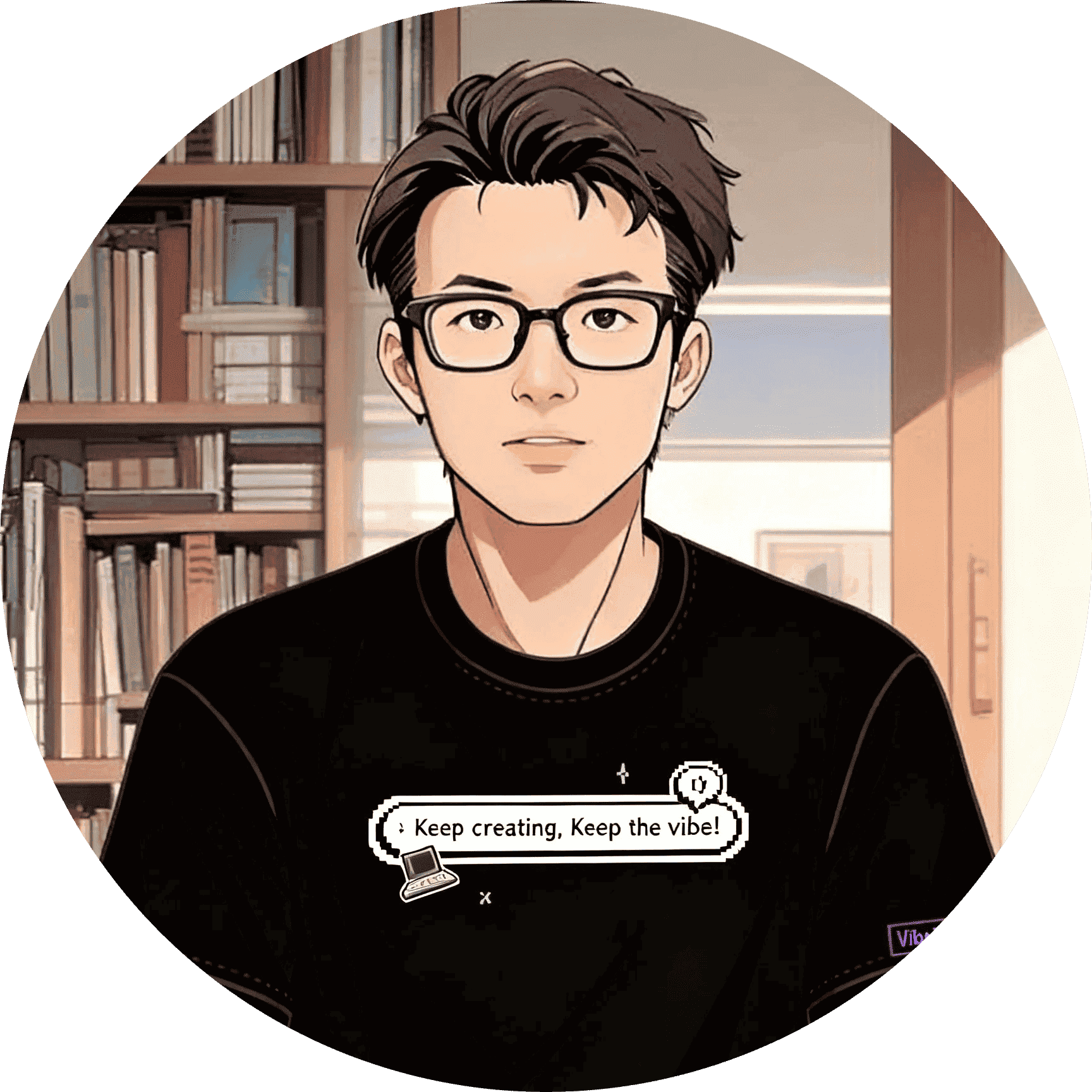 极客杰尼知识库
极客杰尼知识库